|
|
怎么叫的沙堡不知道,可能距离村南的昌源河近吧,积沙成堡。昌源河是沙堡的母亲河,村东流过来,不到二里就出了村西。堡,庄,村,一般老村的地名了如此。浑浊的河水沉淀了细沙,久而久之,河床就高出地面,村南冲积而成的耕地很平展。但垒了两道大堰坝,防止雨季的洪水从南山杀奔下来,给村里造成洪患。依稀听老年人念叨过,河堰决了囗子,曾经漫灌了一村。
沙堡村不大,童年时有两百户人家,不到千把口。发蒙的初始记忆是上世纪60年代初。村里人奔走相告,老少大惊小怪。咱村要安电灯了!点电灯可是划时代的事儿,千百年的皇帝佬也没享用过。一到天黑,住屋里黢黑黢黑的,一盏微光的煤油小灯。老外婆为了省油,捻子还剪的老短,人在屋里彼此看不清脸面,在朦胧中不咸不淡扯几句,马上钻进被窝里入夜。
街门口突然围了一伙人,马车拉过来老长的一根大木头,电线杆子。果真架了线,每户人家也接上了电灯。急躁的等了好几天,终于亮了。还记得清楚,15w的灯泡子,家里装了个小太阳似的。灯下可以白天一样看清人的眉眼,还能做针线活。看书也行,比煤油灯强多了。有了灯亮,婆婆(外祖母)不准看书,还和往常一样撵赶的猴鬼们(孩子)上炕。电灯是好,那是要烧钱的,多点一阵子心疼。
日头落地,见黑就上炕,太阳出来起床。有时候结计办件事要起早贪黑,才起用家里的洋式宝贝——闹钟。闹钟头顶对称的两个铃铛很响。
长辈们说些夜间发生的事儿,总是用三更天五更天,或者头明等老掉牙的土语。童年的觉睡的死,半夜里多大的响动也惊不了美梦。夏天黎明来的快,迷糊中耳根子不清净。炕上就听老外婆和外婆叨歇起来,谁家五更天生个娃,三奴儿,难产呐。老外婆和外婆是沙堡村唯一的接生婆,半夜三更吆喝出去帮人生娃子,那是常见的。去了回来不过一半个时辰。好像掏了个鸟蛋后,匆匆就回来补觉。老外婆有土大夫的手艺,还有有时捎带的看了个病人。瓷片谷草黄裱纸,囗中还念念有词。有时带回的消息“圪森”人,说三更天前街哭闹了一片,是X爷爷病的不行了。
夜间发生的异常事,都是幽灵一般的存在,已经见的多了。
怕的是一大早,叮呤咣当的扰乱。先是老外婆从炕上下了地,忽啷的拉开屋的门拴,倒尿盆子是头件事。沙堡人叫尿盆是足盆子。村里人家,每户不管穷富,都有一方家院。勤快些的,鸡羊猪狗全乎,就是不让养牛马。各有圈舍。早起先伺候家畜。喂食加菜。我们的觉永远睡不够,要从被窝里爬起来穿衣,外婆扯嗓子吼几次才成。上学是件很讨厌的事情。要上早课。
村里人家,都是睡炕长大的。外婆家还算有点光景的,小四合院子有多个归舍。归舍就是住屋,能把几代人分开住。穷些的家庭一个大归舍,靠近里墙一盘大炕,奶奶爹娘孙子,圪挤到一起,根本也不是稀罕的事儿。村里人有句难听的话,穷球儿打的炕洞子响。瓦缸里没啦几两粮。这样的穷寒光景还真见过。土炕是砖垒泥沫的,上边铺一块炕席。厚实的人家铺块隔潮的油布,还在绑绑硬的上面铺层有线毯。白天棉褥靠炕角叠起来。夜间睡时铺开了。小同学中有几户穷人家,晚上睡觉,身子底子连块布单铺不起,几个秃头弟兄共扯着一床被子。有人背地里恶心人,说过的像猪狗人家的日子。小时候已明白些道理,这些人家的光景还真是活的可怜,看到他们都很懒惰,穷不觉苦,缺心眼儿去改变。越穷越吃,越吃越穷。越穷越能生娃。
到了冬天,取暖是头疼的事情。首先是全家人集合在一个归舍,体温也是温,一盘通炕可以挤的热乎。村里人有少数家庭可以买得起煤炭。一大家子人中间围着一眼微弱的煤泥火。为了节约,泥火用铁火柱中间捅个指头粗的火眼。那点儿热量,呵呵。一般人家都是前灶后炕,做晚饭时烟火在土炕里绕几个圈,再从后墙屋顶冒出去。天一黑,趁着热炕钻进被窝,后半夜可就透心的冰凉。
村上的住屋,都是简单的老式窗户竖木格,下方几块玻璃,隔热保暖的窗户纸很薄。一刮风,膨膨的抖动。没见过温度计。但三九寒天,屋里说话,彼此能看到呵出的白气。遇到极寒的时候,早晨起来,当地的足盆子尿水结冰了,门口的水缸,也得用木棍桶开浮着的冰面。光不叽的身子圪缩在被子里,衣裤全压了也不觉得多暖和。冬日好难熬。
农村家家都缺柴火。秋天玉茭,茭子(高粱)收割了,遍野都躺着晒干的秸秆,谷秸。但看着不能拿回家烧。生产队还有巡田的治安队转悠,偷一捆回家那就是坏分子。谷桔拉回到队里场儿上,铡成小段做牛马牲口的草料。玉米高粱秸秆切成小段沤了粪。
生产队的秸秆集体做了处理后,就可见地里到处是拣漏拾柴火的。除了棉花的枯枝可以分户到人家,补充过冬的柴火主要靠菱把。茭把是玉米高粱收割时,留在根部的那一小截秸秆根。地面上有10到20厘米长短的短茬。用小镢头把根部砍出来,叭叭的把泥土在镢把上磕干净。磕茭把的男女,秋冬后在耕地里到处可见。勤快的人家,茭把是柴火做饭烧炕的主要能源。
我和老弟,在10岁上下时,是磕茭把的能手。一箩筐一箩筐的菱把挑回,摞起来码在街门外的院墙根,一直垛到快接近房顶子。有吃的没烧的,自然冬天受罪。懒人家不少见。
童年的时候两怕,一怕三伏天庄稼地里割草。闷在锅里一样的难受,浑身上下汗都溻透了。二怕三九寒天,出门去磕茭把。吃不上喝不足,身体的热量不够,那阵子的冬天格外冷。西北风吹在荒野,泥土打的脸上,风一股一股猛刮,挨了一刀又一刀样生疼。磕茭把时,手伸不岀来,但浑身动起来,就暖和多了。天冷肉皮子缺弹性,寒风中叭叭的磕茭把,手背上就震出无数的微细的血裂子。冻的麻木了,反正也不觉疼痛。回了家缓过来,两手才火烧火燎的丝丝钻心。
村里的娃,不在学校就在地里。玩耍和闲坐的时候少。老外婆眼里揉不进沙子,一见人闲着,她的眼睛就翻起来,噘着嘴嘟囔,太阳底下就是闲的,大白天捧着书看,不动弹。哼,懒断筋,把着本闲书,能吃了还是能喝了…
村里有小学校,每班十几二十人。开始在村中的一座大四合院里,后面是一片不大的操场,安的独一架木头钉成的简易篮球框,还有砖沏成的乒乓球台。教室里的桌椅板凳破旧,课桌三条腿的不少见,找些砖头子垒的支架住不倒。老师上课时,有同学不老实左歪西扭,二人板凳子咔嚓断了,跌滚到地下。拍拍沾满的尘灰,叽叽咕咕一片笑声。有个叫董老师的,眼睛一瞪,吓的猴鬼们都不敢吱声了。董老师还有一绝技。他一边用粉笔和擦子面朝黑板写字,若有同学耍鬼脸淘气的,他立即背过身来,不带瞄准的,粉笔头准确的飞来击中,弹无虚发。淘气鬼们最害怕这一招。
除了冬天,小学校的作息时间和生产队上工时一致。早课,饭时,上午课,吃饭后晌午休息,下午还有两节,然后半下午放学。到天黑给足够多的时间。早放学不是为做作业,每户人家都指望着小劳动力,放下书包,拿起镰刀萝头,到地里给猪掘菜,或者给羊割草。三两一伙结伴,挎着箩头镰刀,欺负土坷拉的命,自小就开始了。春夏还好说,庄稼个头矮,这边望到那头。秋天后玉米高粱没过头顶,钻进去害怕。
养闲人是村里人家的大忌。那阵子还没搞计划生育,生娃是天经地义的平常事。也是怪循环了,越穷越养,越养越穷。从不想活了活不了,家家户户一堆,弟兄姐妹三五个的太多。爹娘生产队上工劳动,扔下站着爬的一堆自由活动。到了七、八岁上,就不能光吃闲饭,喂鸡的养猪的放羊的。伺候好这些家畜,挨到冬天过年前宰杀后卖了,置办些油盐酱醋衣布。哪舍得自家吃掉了,肉多数卖掉,自家留付下水,闻肉腥啃骨头,过几天好日子。
一日三餐,那是不变的故事。早饭时,蹲在十字街的爷们,光膀子的多数。绕着一看,还要问一句,吃甚勒?寡球淡吧,还用问?口诀出来了,庄稼人家,粗面碴碴。一人端着一海碗,圪就靠在墙根下,脚底下小碟子咸菜。玉米碴子熬的稠粥,都是溜着碗边儿喝起,出溜出溜的听着就过瘾。变个饭样,米粥和拌汤。玉米,高粱,小米是主要的食粮。逢节日,或者家里来了远方的亲戚朋友,买一刀猪肉。多日了打回牙祭,吃顿手擀面烙饼等细粮,猫在家里的多。
午饭的种类,基本是千篇一律的,吃高粱面,村里叫茭子面。高粱是诸多农作物产量最高的,短纤维,口感粗涩。和面做成剔尖,擦尖等下口,得掺合大量的榆皮面。木板剔出的茭子面粗,上浇的炒菜没有油水,醋盐主调和,吞咽起来很难。没办法,喂肚皮呢。假如特别的改善了一次细粮,那能摆乎好几天,吃白面赶尖尖了,吃角儿嘞,啧啧,羡慕煞,好活了一顿。村里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家,临走前,家里的日子挤逼的再难过,也要咬紧腮帮子到镇上买斤肉,凑上细粮,给老人吃几顿好饭送上路,那是孝顺。什么是好吃的,提的多的是梨罐头。多次听婆婆说,咽气之前总要问的,想吃甚了?吃瓶梨罐头吧,或桃罐头,大方一回。总算死以前吃过好吃的,不冤了。
可能一千年以前,村上人也是这几句问候语。对面走来,吃嘞没啦?吃嘞,你也吃嘞?吃嘞。再惯些的,又问,吃甚来了…
希望和梦一直离不开肚皮和吃。幸福说起来并不遥远,可老够不着。
(待续)
(图片来自网络)
(via:转载自微信公众号“胡说胡又说”)
|
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资源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,没有账号?立即注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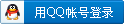
×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