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
|
本帖最后由 池鱼 于 2020-10-20 09:54 编辑
沙堡是晋中盆地的普通小村,住着一代代没过大响动的普通人。
半个世纪前的乡村,已经是集体经济,村里人叫农业社。听历史说,建国后的第一个大节目,政治上是镇压反革命,打倒地富反坏右,经济上叫土改,是打土豪,分田地,把富裕人家剥削的土地分给穷人,贫下中农,还有穷的一毛没有的雇农。按人头均田地。到了1958年河南七里营出现了“人民公社”。分到户的土地集中到村社,一个乡镇为单位变成公社,所以此后老百姓几十年叫农民为“社员”。每个村叫生产大队,生产大队下面有生产队。生产队是基本的核算单位。1958年还弄过共产主义的早期模型。各家各户把灶火熄灭了,全村人吃集体食堂。集体食堂办的时间不长,光听说是糟糕的一塌糊涂,稀湯寡水,都叫喊吃不饱,把人饿煞呀。集体食堂很快散了伙,各回各家了。
胡说是50年代中后期生的,那段历史没有记忆。当脑子里依稀有大炼钢铁的影子。每户人家所有的大门铁环,衣柜上的铜铁锁头等金属的器具,统统被撬走了炼了钢铁。(那些铜铁器具锁头,有的是明清时代,甚至更早的古代制作,是珍稀的文物啊!)
墙上的标语刷的很多,如“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万岁”,“打倒美帝,赶英超美”等。
缺吃没喝的,是那个时期的主旋律。后来听说1960年大饥荒饿死几百万人,但沙堡人还不至于。每年春节后到5月份,青黄不接时,经常听说谁家没粮了,到处求人借吃的。稀汤寡水灌大肚,挺挺都过来了,没听说饿煞哪一个。讨吃要饭的倒是经常见。
穷,一直是童年记忆的主调。听成年人说笑,如果有张油油烙饼,赖后生也能把好看的奴儿哄上走了。
沙堡村有不到一千人口,分了两个生产队。像贾令那么大村,记得是12个生产队。老沙堡西半村是一队,东半村是二队。全村计有2千亩左右的耕地,每队各分一半,人均有两亩来地。那时刚出现了化肥,好东西。社员叫“肥田粉”。白面子撒在地里,能增产好几成。一般庄稼的亩产也就几百斤。除了交了公粮,每个大小社员能均分3到4百斤毛粮。受苦人一天到头都在劳动,又没有油水,十天半月能闻到点儿肉腥味的,那是好人家。越吃越穷,越穷越吃。尤其家里养几个半头小子,能把一座山吃塌了。记得村东头小同学叫“蛮儿”的,一字儿5个秃头兄弟,早起一大锅玉茭面渣渣煮疙瘩,一眨眼就刮干了锅底。
外婆家靠近后街勒,属于二队。爹娘在外工作,我们兄妹一生下就是城市人,户口在榆次,吃供应粮。随年龄增长每月十几斤到20来斤,3两油,25%的细粮,其余是高粱面,玉茭面,小米。还好,一家人滚在一起能调剂。母亲抠出些零花钱补贴家用。家里有现钱花那是令人羡慕的。就这样,耳朵里经常听外婆念叨没钱,没钱。贾令镇赶会,咬着牙给我们两毛钱,把村里小伙计们给眼气的不得了。
祖祖辈辈的沙堡人,生活在这个小村,有的穷,有的富。勤俭持家的,手脚勤快的,日子总是过的好些。有本事的,从土地上走出去,做个小买卖人,或者傍个财东给人打工,总要比守住炕头不动的人日子好。祁县是明清时期晋商的大本营之一。走南闯北,带动了工商业文化,外面世界的信息也带回来。发达的地方不是占了风水,是动,是把风水搅动起来。
沙堡村没有出现过有名的大财主,村里的不少长辈,出去打工做伙计的不少。笔者的老外公,就是太谷有名的“三多堂”的小伙计。伙计是做贸易的业务员。足迹从张家口做到蒙古库伦,又从库伦到中俄边界的恰克图。买卖人出了门像上了战场。习惯了几年不回家。后来没了老外公的音讯。解放前到三多堂打听,说可能到了苏联的毛斯圪瓦(莫斯科)。1956年,村里曾接到来自毛斯圪瓦的长途电话,等到家人赶去大队部接起时,国际长途已断了。以后至死也没有消息回来,老外婆只能默默守活寡到底。以前一说外国,那就是在天上,就是天地间遥远不可及的距离。晋商做生意发财,那阵子顶的风险很大,到蒙古,到大西北,到俄罗斯,累死的病死的饿死的不计其数。老外公失踪后,三多堂那时也衰落了,财东很仁义,赔给了老外婆一些银元。家里得生活,用银元购置了20来亩地。玄啊,那阵临近解放了。后来土改,差点弄了顶地主富农的帽子。一不小心背了时运,就入了″坏人″的行列。
老祁县的乡村,除了做贸易的多,还有许多加工的作坊。如贾令镇的″肉坊″有多家,做的″贾令熏肉”名气很大。沙堡村也有名头,十里八乡的一听说,拉儿的人勒,沙堡的。口诀就来了,"沙堡俩,卖豆芽″。说沙堡村的人擅长发豆芽。做牙芽买卖,估计是明清时代的遗产了。我们眼里没看到过,绝迹了。
半个世纪前的乡村一个模式,集体的土地,社员们一起种。号令大家的,是生产队院里高架的广播喇叭。天不亮,叫醒的音乐吱勒哇啦的聒噪开了。然后分别布置,″一队的社员们,今日到老爷庙后面锄谷儿勒",″二队的奴儿们,到老堰地勒掐棉花…。”
集体经济大锅饭,人活的简单。分粮分油分菜,也不用付现钱,先记下帐,等秋后生产队统一算帐。
社员们种地,经常还一出勤两送饭,看到忙的不得了。粮食产量就那么点儿,但年年听说大丰收。固在地里的社员反正也出不去,顶多往县城转一遭。再远些到城市,得到生产大队开证明。住旅馆或办事儿没证明万万不行。
沙堡村的阶级斗争一直没间断过。1964年的“四清”运动,刚消停了些“文革”就来了。村里也出现了许多红袖章,造反派。闹腾的把东头的菩萨庙拆了,北圪道的五道庙,西头的老爷庙砸了。村里的黑“五类”被揪出来游街,开会斗争。白天劳动了,黑夜经常召集在大队开会。上头哇啦哇啦的宣讲,社员靠着墙根,呼噜呼噜的睡觉声一片。一说开会斗争,听年纪大些的说,唉呀,又家败呀。
半个世纪过去了,前街有个叫“煤漆三”的人老忘不了。他是村里有手艺的人,会油漆墙面美术工,特别是写的一手好字。村里墙上的标语,都是他一个人写的。全村男女都羡慕他,不用下地劳动,工分挣的不低。每天提着两个桶,兴的不得了。白石灰水,红广告色,写不迭的写。人家叫骂谁他就打倒谁,让歌颂谁,他就不断地写万岁。硬看着煤漆三从青春岁月,写的头上有了白发,脸上满是皱纹。
村里人穷苦,说贫下中农,反倒有理踏实。自觉活的还不赖,因为眼里看到,还有比自己更倒霉的。沙堡村没有“右派”,坏人是地主,富农,反革命,坏分子四类。四类分子被斗的落花流水,造反派想怎么折磨也行。不管数九寒天酷暑三伏,四类分子后半夜就得爬起来,扫大街。看着那些个老弱的坏人有时拖着病体干活,心里挺难受。嘴里也不敢说同情,阶级立场歪了要出大事儿的。
村里活的好些的,还是数大队干部。每天也不用做力气活,背着手到地里转转,场儿上悠悠,吆三喝五的挺体面。还有一种活计也让人眼气煞,做队里的巡田的。巡田就是在地里串来串去的巡逻,身上带着镰刀和简单武器,村里的土警察,任务就是防贼捉贼。穷了就贼多,地里的秸杆,树上熟了的果实,长成的庄稼,谁都想往家里偷。巡田的肯定是队干部的亲信了。那活计好就好在自己拿太方便,不叫偷。吃喝比别人家滋润的多。
那时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不放松。家里养多少只鸡,几头猪是有规定的。不按规定养的多了要革命的。现在讲究防疫健康,那阵子来个鸡瘟猪瘟的,虽然损失了收入,却是家人的口福。谁家也不舍埋掉扔了,病鸡病猪统统要煮的吃了。生产大队养的骡马大牲口得病死了,秘密埋葬了也会被人挖走的。
一个穷字,所以什么也不讲究,只要活着就行。
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,沙堡人就是这么过日子。
(via:转载自微信公众号“胡说胡又说”)
(待续)
|
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资源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,没有账号?立即注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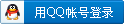
×
|